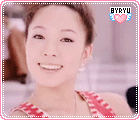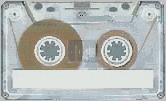所幸隨著人類文明的提升和歷史的教訓,在證明人並非無藥可救的同時,人類開始關注安全的問題,探討使人遠離威脅的方法。無論是否受到現代戰爭造成的大量死傷所影響,安全研究是人類試圖擺脫戰爭的方式之一,從中再發掘外交、互信、衝突管理等手段遏止暴力的發生。戰爭和安全的關聯是假設人類的爭執無可避免,必須透過各種方式防止暴力的發生,藉此達到人身安全。然而,透過人為努力防止戰爭,在大部分的歷史經驗裡不盡然有效,因為在人仍充滿無窮慾望的情形下,所有的努力取得的可能只是短暫的和平,在心靈尚未洗滌之前,人類的行動皆治標不治本,流於膚淺地帶過和平的問題。
事實是人非聖賢。因此在言詞不流於過分理想化的前提下,人類是否有能力達成長期(甚至永久)和平?我認為,答案可能在於基本思維的轉變。依照前述邏輯推論,製造安全基本上是對暴力的回應,但是回應和問題是相對的概念,回應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問題,有問題才有回應。換言之,將希望寄託在回應是不夠的,除非回應的腳步跟得上問題的變化。若把「長期和平」視為目標,實踐和平(終止戰爭)的方法可能必須直搗人心,唯有人性的改變才有機會創造和平。「絕對」(absolute)與「相對」(relative)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甚為重要,只可惜在國際關係習慣以單一角度切入問題的情形下,往往沒有空間採取更折衷的觀點。
絕對與相對
國際關係的發展經歷數次辯論,其中以現實和自由主義學派之間的辯論最為激烈,而延續至今,兩者之間的討論大幅地充實國際關係的內涵。在現實和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以後,後續研究者便陸續被歸類在兩條脈絡其中,直到建構主義的出現,國際關係才又擁有另一種思想。在此種基於方便學習而產生的歸類下,較傾向於某種思想的學者便被貼上「絕對」的標籤,而宛如思想靜止、無法發展一般,現實主義者「絕對」沒有(或很少有)合作的想法,自由主義者則完全不現實。這也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問題之一:各派說詞皆言之有理、自成一家,但整體結果可能是「瞎子摸象」,誰也沒有辦法全盤瞭解真相。然而,更大的問題可能在於摒棄絕對和相對的概念以後,研究者容易陷入以偏狹的框架詮釋現象的陷阱中,進而造成以一概全的誤解或與事實有所出入的推論。當然,最終的解釋涉及個人的價值判斷,但是鮮少有「絕對正確」的說法。在充斥著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學中,個人至少該擁有一絲「相對」樂觀或自由的空間,去評估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偉大的思想家中不乏擁有多重思路者。
學者華茲(Kenneth Waltz)以結構現實主義著稱,但是其也有較不現實的一面。至少華茲在哥倫比亞大學甫取得博士學位時,其論文「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的首章,清楚地指出絕對和相對的概念。雖然在主張對國際現勢的發展感到樂觀或悲觀僅有程度之分後,或許作者基於結構現實主義的立場而必須捍衛其觀點,但是當冷戰結束挑戰所有國際關係理論時,作者在眾說紛紜中並沒有立即澄清對現勢發展的看法。後續研究者在歷史的殷鑑下,或許可以對華茲的觀點大肆踏伐,但作者更大的用意在於「結構」對國際關係擁有「相對」重要的影響,即使其論點未能準確預測兩極體系的崩解。
此外,經濟學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雖然提出自由經濟學的原理,其未必如普遍對資本主義的認知一般,認為個人僅應該追求經濟利益,市場的有效運作即代表個人福祉的最大化。斯密作為經濟學家的同時,也兼具哲學家的身分,「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是其闡述個人道德的代表作。斯密似乎未曾明確指出放任經濟(laissez faire)是助長個人發展唯一的方式,但是在自由主義從冷戰意識形態之爭脫穎而出以後,自由放任成為人類發展的真理,市場更與個人道德融合為「市場教條主義」(所謂個人道德體現在自由資本主義)。或許相對市場而言,道德觀的實用性太低、內涵也太複雜,在自由資本主義正值昌盛的後冷戰時期(尤其是其又有「民主」作為後盾),道德逐漸被大眾淡忘。然而,將市場和個人道德掛勾的謬誤可能是,或許兩者並不相干,而即使相干,道德也並非市場的附屬品。對於亞當‧斯密的誤解可說是以「絕對」的角度視其為「經濟學之父」而犯的錯誤。
個人的絕對與相對和平
或許由於國際關係關注的主體是國家,在放眼如何透過制度規範國家行為時,往往可能忽略個人對和平的影響。畢竟制度由人設計,倘若設計者的考量不是針對參與者的整體利益,制度非常有機會出現缺陷,進而加深問題本身。回顧歷史,國家聯盟即是制度遭人為因素牽制的顯例。雖然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創造和平的十四點計畫,但是以羅吉(Henry Cabot Lodge)為首的在野人士和多數的美國民眾顯然持相反的意見,堅持美國應該以發展自身利益為主,毋須插手歐洲事務。美國未能加入國聯對制度產生嚴重的衝擊,而英、法兩國領袖在巴黎和會與威爾遜意見相左,則使得落實和平的機會更形渺茫。最終的結果是國際聯盟的無能,戰勝國對德國開出極為苛刻的賠償條件,導致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崛起,創造和平的計畫以失敗收場。長期以來,後人對這段歷史的大哉問是:若戰勝國領袖能以世界和平為共同目標,考慮得更遠,是否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答案可能在於絕對和相對的考量。
就個人層次而言,這段歷史突顯的是「缺乏同理心」的情形。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告訴世人,道德和同理心在現實政治中沒有地位,但如果將和平設為共同追求的價值時,現實主義思維的功效有限,因為個人的利益考量仍將大於整體。立基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思想上的現實主義主張人性是自私的,而依該主張推論出來的結果即是以個人為優先考量,與他人角逐相對利益。然而,學者亞瑟羅德(Robert Axelrod)透過電腦實驗指出,個人還是可以透過「以牙還牙」(tit-for-tat)的方式在現實世界裡達成合作,關鍵在於對「未來陰影的考量」(shadow of the future)和釋出第一步的善意。假設和平是全體人類(或多數人)的共同憧憬,在和平作為無法分割的共同價值(common value)的前提下,和平是某種程度的絕對利益。唯有個人率先釋放合作的善意後,和平的理想才有可能在每個人的努力下實現。
金錢作為可量化和分割的資源,或許可透過相對利益考量進行追求,但是世界和平作為共同價值,必須以絕對利益為出發點。從某個角度而言,美國戰後的孤立主義出自於國家和個人經濟利益的現實考量,並在地緣優勢的庇護下,對「安全」形成誤解,將「和平」視為歐洲事務。為了確保和平,英、法兩國將道德負擔沉重的戰爭罪和巨額賠款加諸於德國,企圖予以德國強力的一擊,使其長期不得復甦。此作為反映當時對「未來陰影」缺乏考量,因為在德國於戰後依舊存在歐洲大陸的事實下,各國無法避免未來仍然須與德國打交道。再者,美國無法參與國聯使英、法兩國高度不滿,「以牙還牙」的運作下便是國際聯盟的不力,各大國任由新制度沉淪。此段歷史的教訓是,偏狹的思維導致各方不願釋出善意,和平自然落於幻想,而一時的錯誤造成的是另一齣人類的悲劇。
國家的絕對與相對和平
由於國家由個人組成,若個人能取得和平,則國家必然得以和平。然而,個人如何取得和平?問題的部份答案致少在於解決貧窮和經濟所得的提升。此論述又回到自由放任經濟的主張,即個人追求最大的經濟福祉是道德的,而政府唯一的角色僅在保障財產權和落實法律規範。但是即便如此,貧窮問題並沒有因為自由經濟的落實而獲得解決,反而是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日漸惡化。就貧窮而言,絕對與相對的概念甚為重要。或許人類的平均所得就一個世紀以前有所提升,但在通貨膨脹和人口平行成長的情形下,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發展困境或許終究會實現。市場完全競爭的理念是,個人可以透過比較利益法則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但此種論述的盲點是完全競爭只是理想型,並不存在現實世界。
完全競爭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誤導許多人對經濟運作的理解,未能體認在個人競爭條件不平等的情形下,大型企業和銀行家等足以影響經濟結構者,往往是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大的贏家,對自由經濟的批評因此也不無道理。對於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前諾貝爾獎得主史底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便曾提出「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概念,抨擊大眾經濟學的錯誤假設。實際上,個人在現實世界中掌握的經濟資訊是不同的,因此對體系擁有充分資訊的個人自然佔有相對優勢。換言之,由於資訊不對稱,自由經濟也不存在公平競爭,而倘若持續信奉自由放任主義的原則,其中必有部分的社會公義被犧牲掉。當多數人接受自由經濟學並認為自由放任即是真理時,諸如貧富差距等問題便容易被社會忽略,企業和銀行家等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會將問題輕描淡寫。
「資訊不對稱」指出的是相對的概念,而透過對體制的把持,有能力影響結構的個體便得以透過制定規範把資訊上的優勢化為絕對優勢。此種體系對原本就落後的個體的影響是造成結構上的限制,不僅導致「相對貧窮」,也導致「絕對貧窮」的困境。某領導者曾將國內貧富差距的問題與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類比,其犯的錯誤便是忽視絕對貧窮的問題。國家內部如此,國際體系的運作亦然,無怪乎部份地區和個人逐漸「左轉」,接受社會主義教條。左派對體制的影響是鼓勵抗爭,以推翻自由秩序,兩者對抗的結果便是打破和平。由此可見「從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的重要性,無法僅限縮於個人自私的思考。
我們是否可以和平?
本文的重點在於指出「絕對」與「相對」的概念對於思考和平的重要性。然而,即使有前車之鑑,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仍被許多人牢牢抓住,並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運作。本文突顯將「自私」視為理性的問題;顯然以此種思考為出發點,勢必難以達成世界和平。但是若能透過教育,強調「將心比心」和相對思考的重要性,即使絕對和平仍為能以實現的崇高理想,人類世界可能在更多人擁有和平觀以後,相對更為和平。